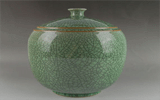山西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省份,每一提及,人们自然就想到山西的煤和山西的老陈醋,山西的煤产量在全国首屈一指,山西的醋则是寻常人家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佐料,但这仅仅是一些最粗浅的表象认识。山西的内涵远非于此,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所具有的丰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其它地区望尘莫及的。五天的匆匆行程,无异于走马观花,屐履到处,所得的也不过是些零碎的片断,但我试图通过手中的一支涩笔,记录我的所见所感,向人们展示我眼里一个真实的山西。
白杨树
从太原到大同,走高速公路要足足四个小时。
窗外开阔的平原,一望无际,道路的两侧,一排排树木整整齐齐,像列队站立的士兵,树冠并不大,一阵风吹过,树上一朵朵的白花格外漂亮,就像雪花轻轻飘落其上。我没有见过这种树,以前曾读过孙犁老先生的文章,写家乡的槐树,里面流露出淡淡的乡愁,精彩至极,我想当然地认定这就是他老人家笔下的槐树。但最终我还是请教了一下当地的导游,导游听了我的话后,乐不可支:“这哪里是什么槐树,这是我们北方最常见的白杨树!”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白花其实只是一种假象,白杨树叶的背面是银白色的,风卷起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远远望去,不就是朵朵绽放的白花吗?
白杨树,我猛一听到这熟悉的字眼,就想到初中时曾读过的茅盾先生佳作《白杨礼赞》:“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其实茅盾先生是见景生情,以树喻人,借白杨树赞美那些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抵抗日寇侵略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普通老百姓,细致入微的描写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时隔十五年后,我仍能清晰地记得这些精美的段落。我常常默想着白杨树的样子,但却一直无缘亲见,如今有幸第一次踏上北方的土地,见到向往已久的白杨树,那份欣喜,自然难以言表。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风物何尝不是如此?白杨树是不太讲究生存条件的,大路边,田埂旁,哪里有黄土,哪里就有它的生存。它不追逐雨水,不贪恋阳光,只要能够在哪怕板结的土地上,给一点水分,白杨树就会生根、抽芽,这也正与北方寒冷干旱的气候相适宜。“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不是亲到山西,也许像我这样的南方人,还会继续把白杨当作槐树的笑话呢!
云岗石窟
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位于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
云冈石窟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我印象中的北魏,是北朝时由鲜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一位北魏君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便是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即是他的不凡之举。由于平城(今大同)位置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洛阳,虽然其间也遭到一些贵族的极力反对,但成竹在胸的孝文帝最终还是摆平了他们,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他还杀了带头反对的太子。另一方面他十分崇尚中原文化,积极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表现出他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这样一位英明之君,同时也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洛阳龙门石窟就是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在崇信佛教这一点上,历代的北魏君主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不惜耗费大量的国力,来延续这项庞大的工程了。
云岗石窟中第二十窟,造像完全露天,立像是三大佛,正中的释迦坐像,高13.7米,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浑厚,气魄雄伟,为其代表作。我们所见到的关于云岗石窟的宣传图册,选取的大多是这尊佛像。其实之前它并不是露天的,也曾筑有窟前带,但在辽代以前不幸崩塌。
为了保护这些石窟,使石窟免于风吹日晒雨淋,当时的建造者可谓煞费苦心,窟前或建四五层楼阁或三四层木构窟檐,朱红柱栏,琉璃瓦顶,工艺精巧、色彩浓郁。但岁月沧桑,一千五百年来,石头风化剥蚀自是难免,即便是那些巨幅佛像,手足耳鼻等部位,也多有缺失之处,一些小的,甚至已面目全非。更何况兼有人祸,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一千四百多个,斧凿遗痕,至今犹在。
我不知当年北魏君主建造这些石窟,是不是为了佛之不朽,即便选择了坚硬如石头这样的材质,最终仍无法抵挡岁月犀利的刻刀。若干千年之后,我们的后人是否还能再见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呢,谁也无法预料,一行人谈论着,感叹不已。
北岳恒山
一般寺庙大都建于平坦之处,恒山悬空寺却反其道而行之,建在绝壁上,悬于半空中。悬空寺共有殿阁四十间,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虚实相生,寺内有铜、铁、石、泥佛像八十多尊。远望悬空寺,像一副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万仞峭壁间,近看悬空寺,大有凌空欲飞之势。登临悬空寺,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几经周折,忽上忽下,左右回旋,仰视一线青天,俯首而视,峡水长流,叮咚成曲,如置身于九天宫阙。当年唐代诗仙李白游历至此,连连称奇,遂在山下岩石上题写了“壮观”二字,终究是诗人本性,“壮”字却多写了一点,据说是比它处更胜一筹的意思。
悬空寺的设计与选址,可谓匠心独具,悬空寺悬挂于石崖中间,石崖顶峰突出部分好像一把伞,使古寺免受雨水冲刷。山下的洪水泛滥时,也免于被淹。四周的群山也减少了阳光的照射时间。有此三者,悬空寺得以保存完好。
说到悬空寺的奇,不能不提最高层的三教殿,内中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的塑像共居一室,按常理,各派宗教大多互为排斥,佛教、道教、儒教始祖同居一室,和平共处,确不多见。
悬空寺虽险峻,但登临一番,半个小时已绰绰有余,我以为恒山也不过如此,导游却告诉我们其实还未到真正的恒山脚下,上恒山还早着呢!绕了好几个圈,车子终于抵达恒山脚下的停旨岭停车场,抬头仰望,只见群峰巍峨耸峙,气势雄伟。我们乘缆车上山,越往上走,心中越发战战兢兢,深不见底的峡谷,山风呼号而来,那声音势如虎啸,几位女士早已吓得不敢向下看一眼,等缆车到达终点,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当地的导游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甚是健谈,一路娓娓道来:恒山以奇险著称。整个景区如诗如画,令游客如置身于世外桃源,流连驻足。四千年前,舜帝巡狩四方,来到恒山,看到这里山势险峻,峰奇壁立,遂封恒山为北岳。秦始皇时,朝封天下12名山,恒山被推崇为天下第二山。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曾到恒山巡视、祭奠。以后的历代帝王,也都差使臣到恒山朝圣。许多文人学者对恒山都有过动人的描绘,汉代历史学家班固有“望常山之峻峨,登北岳之高游”的佳句,唐代贾岛《北岳庙》)诗中有“天地有五岳,恒山居其北,岩峦叠力重,诡怪浩难测”的赞叹。
我环顾四周,见山中树木并不茂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稀疏,远不如我曾去过的黄山草木葱茏,倒是那一片片光秃秃的赭色山石不时赫然入目,显得有几分荒凉,失望之情立形于色。导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介绍说相关部门对恒山的生态保护极为重视,随后指了指左边的一片松树林,说:“这就是飞播造林后长成的!但山西终究缺水,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所生活的江南被喻为水做的,是流动的碧水,使江南充满了灵性与韵味,而山西每年仅500毫米的降雨量,多少使得它有些捉襟见肘。我不禁庆幸自己身居江南。
恒山以道教闻名,据记载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五洞天,茅山道的祖师大茅真君茅盈曾于汉时入山隐居修炼数载,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亦曾修道于此。我们去了紫微宫、白虎观、纯阳宫等处,与五台山寺庙里游人如织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是,这些道观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只有我们寥寥十几人。大家探究其中原由,董君一语惊人:“岂不闻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想想也是,佛教自东汉时从印度传入我国,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鸿儒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它的信仰深入了民间,“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正是真实的写照;而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属于土生土长,虽也在某些朝代一度被推崇,但就受帝王重视程度而言,却远远不及佛教,自然也就很难兴盛了。
最后还得说一说苦甜井,这恒山中的奇景。井位于恒山半腰,双井并列,相隔1米,水质却迥然不同。一井水如甘露,甜美清凉,水井深数尺,取之不尽,可供万人饮用,唐玄宗李隆基赐匾“龙泉观”。另一井水苦涩难饮,形成鲜明对比,现苦井已封。苦尽方能甘来,不知这两口井是否就暗合这样的深意?
五台山
五台山的人气极旺,终年香火缭绕、梵音不断,原因不外乎它是全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我们曾见到一位女性佛教信徒,以最虔诚的五体投地礼一路叩拜而来,让人很是敬佩她的执着。
五台山方圆约300公里,因五峰如五根擎天大柱,拔地崛起,巍然矗立,峰顶平坦如台,故名五台。山以东、南、西、北、中五座平台形的山峰环抱而成。据导游介绍,五台山的寺庙有140多座,而我们所去的仅是其中最知名的五座,如今我已分不清这些寺庙各自不同的格局,只记住了它们的名称,比如佛光寺、南禅寺、显通寺等等。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塔院寺内的藏式舍利塔,塔高60多米,极为庄严雄伟。108级台阶直通顶端,气势雄伟,登顶远望,美景尽收眼底,为全山远眺最佳之处。听到导游充满诱惑力的话语时,我不由得怦然心动,欲一登为快,但不知何故,竟不得而入,空欢喜一场,我不禁悻悻然。
令我颇感兴趣的是一些历史人物与五台山的渊源,据说清顺治帝、宋杨五郎、鲁智深等都在此出家,尤其是顺治帝的故事更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关于顺治出家的通常版本是:由于多尔衮摄政,顺治苦熬了多年傀儡皇帝的生活,加之与皇后不睦,这使他一度消极厌世。董鄂(董鄂并非秦淮名妓董小宛,已为史家证实。)的出现,使顺治“火热爱恋”,激起了他生活的波澜。正因为这样,当顺治十五年正月,宠妃董鄂所生的唯一皇子夭亡,两年半后的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也突然病死后,顺治痛不欲生,万念俱灰,再加连年战争和宫廷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他饱尝了恐、恼、悲、狂等烦恼之苦,终于萌发了遁入空门的念头。孝庄皇太后听说后,怒气填胸,要他以国家社稷江山为重,打消出家的念头。可是顺治铁了心肠,再不恋红尘,他亲手把自己的头发剪去,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偷偷逃出皇宫,去了五台山,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从此开始了青灯黄绢的僧侣生涯。
清朝宫廷始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这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我一直不解的是身居北京紫禁城内的顺治皇帝何以能神不知鬼不觉通过重重守卫,只身来到五台山,而之后康熙虽数次寻访,却终不得而见,至今我尚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正是众多的史学家所置疑的,他们坚定地认为,顺治帝出家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顺治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终年二十四岁,病因可能是天花。其火化后的骨灰,被安葬在位于河北遵化县的清孝陵。
当然那些纷至沓来的游客,根本就无意去作这样严谨的考证,他们更乐意在对所谓的顺治和康熙遗迹的探访中,去满足常人固有的那一份好奇。
平遥古城
去山西之前,我特意翻阅了摄影师黑明的《古城平遥》一书,为的是增加一些对平遥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当我身临其境时,除了惊叹便是深深的震撼:这座建于西周宣王时期,距今已有2700年历史的古城,中间曾经历几多天灾和兵火的洗礼,而今却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这也就不难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所作的高度评价:“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平遥古城令人为之叫绝的是它的设计,据说创意来自乌龟:城门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城池南门为龟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双双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唯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径直向东开,据说是造城时恐怕乌龟爬走,将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台上。这个看似虚妄的传说,折射出古人对乌龟的极其崇拜之情。乌龟乃长寿之物,在古人心目中如同神灵一样圣洁。它凝示着希冀借龟神之力,使平遥古城坚如磐石,安然无恙,永世长存的深刻含义。
乌龟其实是很有灵气的动物,但在今天,它却遭受了不应有的委屈,譬如“乌龟王八蛋”、“龟孙子”之类的咒人粗话,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实在是辱没了它的本性。
说到平遥古城,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阮仪三教授,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平遥。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典故事:1981年初,阮仪三与同事一起到山西榆次市协助城市规划工作时,平遥县的工程师们将一份《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送给同济大学老师们征求意见。阮仪三看后心里一沉:因为这份规划要在古城内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城墙上要挖开8个大口子,还要将古市楼周围的房屋拆掉,做成一个环行的交叉口。如果按这个规划实施,平遥古城将被破坏殆尽。阮仪三心急火燎赶到平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古城东面已经按此规划在城墙上扒开一个口子,正在拓宽马路,拆去了两旁180米长的传统民居房屋。阮仪三立即建议停止这种所谓“建设性的破坏”工作,并和山西省建设委员会商定,由同济大学来协助平遥县重新规划。7月初,阮仪三挑选了10名能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开赴平遥,重新编制规划。在规划中确定了“新旧区绝然分开,确保老城,发展新城”建设方针。此后,建设部高级工程师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罗哲文等有影响的老专家也闻讯赶到平遥。郑老在阮先生的保护古城规划方案上评议说: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山西省很快批复了这个规划,平遥古城于是被保存了下来。
说实话,我很佩服与敬重像阮仪三这样的专家学者,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渊博的学识,对于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更在于他们在大建设的背景下,在不被人理解的困境中,不盲目跟风附和,而是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与独立。只是像这样的专家学者,如今已越来越少。于是乎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对专家学者们的批评与诟病,看到更多的是像拆毁平遥古城这样的荒唐闹剧仍不时上演,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的出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得益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等几部影视剧的热播。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
乔家大院是俗称,它的宅名叫“在中堂”,房主人的名字叫乔致庸。乔家如何有财力能建这么大的宅院呢?这要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说起。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不得不寄食在舅舅家中。由于舅母的歧视,乔贵发长大后回到乔家堡村独立生活。有一次,村中有人娶亲,他前去帮忙,不料迟到一步,便受到管事人的冷言冷语讽刺。血气方刚的乔贵发,一怒之下便去了口外,在包头苦捱了30年。最初,在包头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的合成当铺做店员。店员中有一个姓秦的山西老乡,两人一见如故,便结为异姓兄弟。十多年后,两人稍有积蓄,便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乔、秦二人能审时度势,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从经营豆腐、烧饼以及零星杂货,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由于待人接物好,又善管理,生意日见兴隆。在这蒸蒸日上的生意面前,乔贵发及其后代恪守祖训,经常警惕奋发,力求持盈保泰,不断发展。秦家子弟恰恰相反,吃喝嫖赌,生活骄奢淫逸,终于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好逐次从号内抽出本金。秦家抽出的本金均由乔家补进,秦家抽一股,乔家往里补一股,最后,两家合资的生意成了乔家的独资生意。
乔贵发的发家史,其实就是一部晋商创业史的缩影,他们将诚信飘在古朴的幌子上,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印在荒山古道上,将创业的荣耀记录在发黄的家谱上,构成了中国三大著名商派之一的“晋商”现象。诚如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孔祥毅教授所说“晋商在其近五百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经营宝训,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遗产。500年间,晋商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足迹遍华夏,声名振欧亚,影响之大,在中国、在亚洲甚至于世界商史上都有一定的位置。”
乔家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商界,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乔家也是目光独到。当时山西晋中一带以经商为荣,子女中最有才能者首选经商,次一等的才读书求仕,以致连一些秀才也投笔从商,到后来竟然出现连参加科举考试的额定人数都凑不齐的尴尬局面。官府无奈,只好临时从票号中找一些书法较好的店员充数。而乔家却一扫陋俗,以私塾的形式延请教师,在中堂家塾的教师都是有名气的饱学之士,待遇十分优厚,民国19年(1931年)为年薪200块银元,年敬、节敬等红包除外。每位教师有两名书童伺候。饮食与主人中最上等的相同,每顿饭都有一位主人陪同,逢年过节要设专筵招待,宴请亲朋时一定要请教师坐正席。放学时教师回家都有轿车接送,主人们一字排开送到大门以外,等教师上车后才回去。
乔家对教师礼遇有加,教师自然感恩戴德,倾其所学。因此乔氏子弟多数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映字辈”上过大学的就有2人,第七代兄弟20多人中,则有12个大学生,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学位者3人。还有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由此可见,乔家主人的远见卓识。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抱愧山西》,之所以惭愧,是由于之前对山西的误解与错觉,而我对山西同样报有愧意,以我有限的笔力,只能蜻蜓点水般地记下些流水文字,根本就无法深入地挖掘山西这座蕴藏量极为惊人的巨矿。但我仍斗胆提起笔,是因为心中有一股难以遏制的写作冲动,从任何理由上说,山西都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