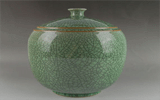四月的一天午后,一封寄自澳大利亚的信件送到我手上,我很纳闷:自己在国外无亲无友,这是怎么回事呢?迫不及待地拆开,一本精美的《澳州彩虹鹦》杂志赫然入目,我的短文《打开水》竟刊登在第十一期上。这是我的文章首次走出国门,心中那份欣喜自然难以言表。
年初,我偶然闯入一个叫澳洲长风论坛的网站,在这里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朋诗友,没有任何名利的纷争与诱惑,大家都以一种平和单纯的心态,进行创作上的交流。我喜欢这样的氛围,闲暇时常去发一些贴子,虽然也知道《澳州彩虹鹦》纸刊会定期在论坛上选稿,但从未奢望那份幸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而无意插柳的我,却捡得了一抹春色。
鼠标轻点,瞬间就完成了投稿,万里之外的澳洲,似乎就近在咫尺。网络的神奇,让我这个二十多年一直默默坚持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感慨万分,一些陈年旧事纷涌而来。
1985年,我还是丽水地区农校的一名学生,“不务正业”的我与很多同龄人一样,狂热地做着作家梦,并偷偷地开始向本地的一些报刊投稿。记得当时有一条一成不变的规定:稿件必须用方格稿纸誉写清楚,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爬格子一词的由来。我生性愚钝,不属于那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快枪手,每写一篇文章,必定要打好草稿,反复修改后再抄写到方格稿纸上。因为担心字迹潦草会被编辑弃之废纸篓,所以我笨人笨办法,总是一笔一划用正楷誉清,一篇千字短文,有时竟耗时一个多小时,弄得手酸人乏,以致于再次面对方格稿纸时,不禁望而生畏。更惨的是,一些稿件寄出后,常常是石沉大海,而我又没有备份的,许多原稿就这样散失了,如今想整理旧作,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徒留遗憾。
大约过了五、六年,小城几家最早的电脑打字店同时开张,对正为抄写所苦的我来说,这不啻于是一个福音,只是每页十元的打字费,价格不菲,让我这个工薪阶层,总感觉囊中羞涩底气不足。好在这样的状况没有延续太长,不久,单位里就添置了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身为文书的我,在频繁的工作交往中,与打字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使得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借机谋一点小小的私利,确切地说,是无形中增加打字员本已不轻的工作量。那段时间,我常常是将文章的草稿往她手中一交了事,而正印证了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时间一长,打字员对于我的信手涂鸦,竟有了超强的识别能力,有时甚至还帮忙改正一两个错字,成了我的“一字之师”。我也不用再往邮局跑,一个传真,稿件就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飞往天南地北,那速度,怎一个“快”字了得!
这些年,在辗转几个单位后,我调到了报社任职,这是一份我十分喜爱的工作,在尽心尽力履职的同时,也可以静心写一些自己的东西。虽然我全拼打字时的手法,被人戏称为“一指禅”,但笃信勤能补拙的我,也渐渐使自己的打字水平有了提高。如今我已在《91文学》、《红袖添香》、《椰树下》等几个文学网站建立了个人文集,想要投稿,只要轻点鼠标,几秒之间就可以轻松搞定,那份从容与惬意,只有经历了这些难忘岁月的文字中人才能深刻体会其中滋味啊!
编辑:季靓 来源:今日龙泉 2008-11-17 15:43 |